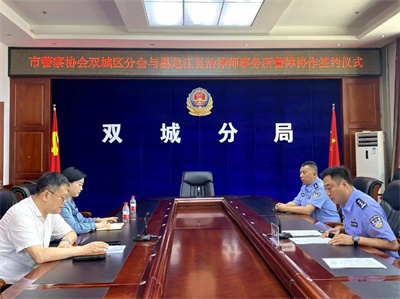月儿圆圆(长篇小说)
第三章
秀芹二十三岁那年,也就是一九七0年秋。
一天晚上,在兄嫂家,通过媒人介绍,秀芹和时任县水泥厂的一名年轻的张来福厂长处上对象。
张来福是独生子,父母都是双职工,在当时的年代,张家已属于“小康”家庭了。
张来福高中毕业的当年考取了省商业学校,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县水泥厂任技术员,小伙子精明能干。第二年就被组织部门任命为厂长助理,正股级干部,第三年,原厂长调任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,他就成了厂 长一职的唯一竞争者,经组织部门考核考察,一个月后他走马上任。当时的张来福是县内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,升任厂长后的第一年企业利润创全县各大企业之首,工作蒸蒸日上。
张来福人长得虽不出众,但有事业心,爱厂如家,常常与工人们滚打在一起。星期天大都在单位度过;他心地善良,待人热情,没有什么官架子,很虚心听取职工对企业的改进意见,全厂上下近百号老少职工无不敬重他。
张来福在和秀芹处对象时,虽年龄已二十六岁。比秀芹大三岁,但对于出生于农村的秀芹来说,各方条件无可挑剔。
“文革”时期男女谈恋爱,可没有现代人的浪漫。虽说他们都居住在县城里,可县城和普通的乡村比较起来似乎没啥两样,就是有孤零零的几栋小楼和几家企业,城里人的住房与农村人差不多,大都是土草房,条件好一些的家庭,也是后来翻盖的砖瓦平房。小城里,没有公园、公共广场可去游玩;晚间街道漆黑一片,没有一处路灯可以照明夜行;只有城东的龙头山可以去踏青,但到了半山腰,人们大都被“弹药重地,闲人止步”的字牌挡住了去路,无不令人扫兴而归;城北的讷谟尔河,在夏季时节人们可以去游泳。但当时的人们思想极其不解放,别说是恋人,就是生活在一起多年的夫妻也没有在一起同游的。小镇真的没有什么可供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去处。
秀芹和张来福的约会,大都在周末的晚上去张的父母家或秀芹的哥哥家小坐一会儿。周天俩人逛逛破旧的城区,在没有水泥路的街道上溜达溜达,除有时下几次饭馆外,很少进商店,那时商店也没啥逛头,日用生活品极缺。也不能去双方的单位约会,免得别人戳脊梁骨说闲话。
就在这种环境下,秀芹他们热恋五个月后,也就在第二年的正月举行了婚礼。
从此,秀芹就不用住在兄嫂家,和公公婆婆东西屋相住。每日里,小两口进进出出有说有笑,一起上下班。张来福每天用自行车接送秀芹。他俩同行在路上,多么令人羡慕,无不夸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。
秀芹下班后回到家中换掉工作期间的衣服,帮助公婆做饭,料理家务,公婆看在眼里喜在心头。平时,公婆、丈夫换下的脏衣服,不用指点,起早贪黑洗净,烫得板板正正的,亲自送给公婆夫君。秀芹闲时,偶尔和夫君去兄嫂家串串门,不忘记给侄男侄女捎点好吃的,侄男侄女都很喜欢她这个老姑。除此之外,不象有些小媳妇东串西串的,陪着公婆聊天,说说心里话。
张来福单位工作很忙,但秀芹从不给他添乱子,有时也帮助夫君策划企业发生规划。她的许多观点备受夫君的青睐,夸她是个贤内助。平时,夫君有应酬,她从不干预,夫君酒喝高了,她就亲手给他调上一杯糖水,烧些温乎水给夫君洗脚。让他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迎接第二日新的工作。
开春了,房前房后的菜园子该伺候了。虽然秀芹出生于农村,可农活对于她来说是陌生的,但她不偷懒,如何翻地备垄种菜栽秧,她都先向公婆请教。每每公婆说种园子的事不用她操心,把工作干好,注意身体就行了。可她执拗要做。她很聪明,一点就会,利用早晚和周天时间与公婆一道把小小的菜园子伺候象花园一样,看着长得旺盛的各色蔬菜,公婆逢人便夸媳妇是个好巧手。
那时候市场经济不发达。城里人想买蔬菜,只好去市区的菜店购买。可她家几乎就不必了。园子里下来的新鲜蔬菜都吃不了,多余的蔬菜除了送亲戚好友外就是烂掉,她觉得很可惜。
一天,秀芹向公婆建议:
“咱们家这么多蔬菜,大部分都白白烂掉了实在可惜,咱们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,换些钱也好充实家里的补给。”
秀芹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允许的,就连农民自产的粮食除了一部分自用外,全部交公粮,谁敢去私卖。蔬菜也一样,那要是被那些红卫兵抓住可不得了。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、“挖社会主义墙角”、“投机倒把”等帽子非给你扣上不可。重者关上你几天,轻者挨一顿臭骂臭打,还要没收你所卖的东西。
公婆听秀芹说得很在理,心动了。仰仗他家的“势力”,那些看街护路的红卫兵也不会对他们怎样的。
公婆同意了秀芹的观点。周天的早上,公婆和秀芹把自家产的蔬菜整整装了一小推车,兴高采烈地去市场销售。购物的市民一见这水灵灵的蔬菜纷纷购买,他们略低于市场的价格,不到一小时的工夫,全车的蔬菜就被抢购一空。正当他们徜徉在喜悦之中的准备返回家的时候,一个戴着红袖章,一身黄军装的年轻人来到他们身边,不由分说要把他们连人带车扣下,非要他们去革委会说个清楚。
秀芹据理力争:
“我们又没有犯法,只是出售自家的蔬菜。”
那红卫兵模样的年轻人瞪着眼说:
“你们这种行为就是犯法,家家都象你们这样做,公家的菜能卖出去吗?再不跟我走,我就喊人把你们绑起来!”
胆小怕事的公婆忙上前解释说:
“小兄弟,看在我们是头一回的份上,放了我们吧,下次我们再不卖了。”
“说的如此轻巧哦,不行!”那红卫兵边嚷边推起小车要走。
秀芹挡住了他的去路,并高喊:
“给我站住!”
“你想造反呀,你是干什么的,你这是妨碍公务。”红卫兵吹胡瞪眼直嚷。
围观的群众不知谁说了一句:
“这姑娘是全县劳模,你也敢对他横!”
“什么劳模不劳模的,她扰乱市场,就该收拾。”年轻人冲着人群直嚷。
“你小子也不看她是谁,打狗还要看主人呢,她可是咱们县最大的企业水泥
厂的张厂长的媳妇,你要是得罪了她,吃不了还得兜着走。”不知何人说了这么一句。
年轻人稍楞,自言自语道:
“她是张厂长的媳妇,不会吧?她怎么能做这玩艺呢,岂不是故意和我过意
不去吗?”
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走过来,冲着年轻人说:“人家卖的是自家产的蔬菜,
又没有倒卖,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“
“你、你,你说谁呢?”年轻人指着老头吼。
“你怎么还想动手打人呢!”围观者一齐指责那年轻人。
“我看你们反了不成,我去革委会找领导,你们等着”。年轻人没有了当初
的嚣张气焰,放下小车,一溜烟走了。围观人哄堂大笑。秀芹和公婆借机推着小车回家了。
这起“风波”后来让张来福知道了。他没有和父母、秀芹生气,还认为做得对。至此以后,秀芹早晚去卖菜,公婆则在周天卖菜,但他们不去市场,大都在街头路边上下班职工经过的地方,也没有什么人来干涉。其实,张来福已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通光了。
转眼到了年末,急于抱孙男孙女的公婆仍不见秀芹显怀。心中那个急呀。但公婆见秀芹每天工作那么忙,家务活又干得头头是道,几次想和她面谈又难以启口。
有一天,也就是秀芹结婚第二年的元旦后的第二天,沉不住气的公婆质疑儿子张来福:
“你们是在搞什么名堂,你和秀芹结婚都七个月了,还不见她有身孕的迹象?”
张来福很理解父母的心情,说:
“我和秀芹正常过生活,有时我们自己也纳闷,也许过一段他就会有的。”
整整一年后,秀芹的身体依旧没有变化。公婆开始对秀芹能否生孩子产生了极大的怀疑。有时,他们见到秀芹,真想发火,但一见眉目清秀的秀芹脸上也开始挂着不悦的表情,依然是那么的勤快,只好把要说的话咽到肚子里。
一天晚上,秀芹问张来福:
“咱们俩是不是有问题?结婚一年了,我怎么还不怀孕,也许我……”
“是啊,父母曾问过我俩的事,我怕上伤了你的自尊,始终未向你提及,不
妨咱们都看看医生”。来福柔和地说。
“要是我真的不能生育,断了你张家的香火,我……”秀芹的话还未说完。张来福一下子捂住她的嘴,神情地对她说:
“阿芹,别说不吉利的话,也许是我有问题,看看医生再说。”
“如果真是我的毛病,你会赶我走吧,我也太不争气了。”秀芹趴在张来福的怀里,泪水涌了出来。
“别哭,我们的结合也不是为了纯粹要孩子,我是多么的爱你,只是父母他们急啊 !”张来福紧紧把秀芹搂在怀里。
结婚一年了,秀芹和张来福恩恩爱爱,从来没有拌过嘴,红过脸,相互照应,相互鼓励,在外人的眼里他们是天生的一对,倍受很多人羡慕。
张来福的父母为了能早日抱上孙男孙女,四处请医生给儿子媳妇看病,可数十个本地或外地的医界专家,都说他俩身体一切正常。
时间又过去了一年,秀芹的身体还是老样。公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不久,一向和蔼可亲的公婆有了情绪,动不动就在秀芹面前摔东西落脸子,搞得秀芹无地自容。但公婆为了不能断了张家的香火,起初还是耐着性子,没有做出太大出格的事,说出难听的话来,还花费了大量的积蓄,让秀芹她俩吃了不少民间偏方,甚至请巫婆来家给他们跳大神,驱赶他俩身上的“恶魔”,企盼奇迹早日出现。可整三年过去了,秀芹的身体依旧那样苗条,肚子始终瘪瘪的,只是面容多了几分憔悴。
张来福的父母急于抱孙子孙女的心情可以理解。可又有谁理解秀芹的心情呢,外面的风言风语也说了不少。耐不住性子的公婆对秀芹的态度逆转了一百八十度,该做的饭不做了,该洗的衣服不洗了,有事没事就找秀芹的茬。有时甚至当秀芹的面骂她是“铁公鸡”、“白骨精”、“扫帚星”。秀芹无奈,也不敢顶嘴,只好整日看着公婆的白眼。那时候,张来福对她虽好,为这事没少和父母理论,可自己不争气。实在忍受不了,就抽空跑到兄嫂面前痛哭一番。兄嫂看在眼里疼在心头,不时地安慰她。自古以来,不生孩子是做女人的大忌。
秀芹总认为自己是幸运的,可未曾想就因为自己不生孩子,在公婆面前整日抬不起头,在同事面前矮了人半截,常常在背后以泪洗面。
最理解、体贴秀芹的当然是夫君张来福,每天看到昔日开朗、勤快的妻子愈变得郁闷、少言寡语时,他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“男人有泪不轻弹,只是未到伤心处”,深夜,她常常陪着秀芹流泪。他是男人,也是父母们的唯一儿子,可以想像他承受的压力比秀芹要大的多。
前几日,张来福的父母找到他,非让他和秀芹离婚不行,不然以死相胁迫。他十分理解父母的内心世界。要是那样,他无颜见秀芹,更会伤秀芹的心。一边是生他养育他的父母,,一边是他心爱的妻子,难道仅仅因为秀芹不生育就与她分手,他的良知会遭到谴责的。为此,他多次背着秀芹与父母抗争,恳求父母再给一段时间看看,可父母总以“不行”的话回击他,他无更多的语言相劝父母。他是一厂之长,又是全县劳动模范,正值年轻有为、事业发达的时候,仅仅因为这事与秀芹分道扬镳,上级组织部门会如何看他,同事们又会在背后议论他什么,不知情的人甚至怀疑自己没有那方面的本事。可这方面的嘀咕确实不少,与之相处很好的同事、朋友也不曾一次与他开玩笑的说:“来福,结婚这些年,咋不见你家嫂子下蛋呢,你是不是个二性子,不行,咱哥们行,别让嫂子背黑锅!”张来福听到这话,为了不失身份,不伤和气,往往选择逃之夭夭。
住在乡下的秀芹父母为此事,曾先后几此找到亲家,抱着一线希望,希望他们再给一定的治疗时间,不但次次碰灰,而且还要带走一箩筐的奚落。秀芹的父母自知女儿的不是,也只能为女儿多流泪。每每见到来福,秀芹的父母总是爱惜的说:
“孩子,苦了你啦,你对秀芹好,我们都知道,可你的压力很大啊,要不然,我们把秀芹领走,你再找一个……”秀芹的父母说到这个时候老泪纵横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一天早上,张来福主动对父母说:
“爸爸妈妈,我看你们也别太计较这事了,你们给秀芹和他们全家施加了多少压力。秀芹是位好媳妇,你们不能否认,仅因不生孩子就将她赶走,与情与理不容啊!”
父亲气急败坏地对他吼道:
“你小子翅膀硬了,当上破厂长就不服天朝管地朝管了,我们的话你也可不听,你让我们张家断了子孙呢,你还是男人吗?咋不为我们想想,没有了香火,叫咱如何在众人面前抬头,你作孽呀!”
“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,这世上不生孩子的男人女人有的是,你们封建传统意识太强,我和秀芹可以抱养一个,把他(她)培养成人,不照样可以接咱张家的户口吗?”张来福尽量心平气和与父亲说话。
“接你个头,你真孬种,娶了一个不下蛋的鸡,当初给你介绍那么多的对象你都不干,娶了她,你图什么。”站在一旁的母亲骂他。
“报养一个,说的轻巧,长大了还不是人家的孩子吗?你这个混球,非要把老子气死!”父亲狠狠嗑了一下烟斗,说着说着还要拿烟斗揍他。
“我说不过你们,那我和秀芹搬出去住好了。”张来福顶撞着。他真的舍不得丢下秀芹。
“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,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抚养成人,到后来成心和我们作对,你不把她赶走,老娘我今天就撞死在你面前。”母亲说完,向墙边走去,真的要撞墙。
张来福气的没有阻拦母亲。正当婆婆要撞上墙的一刹那间,秀芹从外面走进屋子里,一把抱住了婆婆。
“你松开我,一只不下蛋的母鸡,你不配做我的儿媳妇,从现在起,你就不要踏进我老张家的门……”。秀芹忍住泪水,依然紧紧地抱住婆婆,她不想婆婆因为她有个闪失。
“阿芹,松开她,让她死吧,整天无理作闹,让不让人家好好工作,简直就是……”。张来福没好气地说。
“好啊,你这个畜生,你被这个小妖精迷住了,你们走,走的越远越好,别再让我们看见,就当我们没你这个儿子。我的天呢,为何会这样……”母亲指着张来福骂着,挣脱了秀芹,便一屁股坐到地上耍横了。
张来福没有安慰母亲,拉着秀芹走到院内,准备出去。
“你,”公公用手指着秀芹,气的咬牙切齿地说,“我们张家哪八辈欠你的,你不能为我张家传宗接代,留你在这儿也没有用,占着茅坑不拉屎,趁早滚!”公公作了一个“赶”字手势。
“爸爸,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,愿你儿子没有本事好了。”
张来福接着对泪流满面的秀芹说:
“让他们闹去吧,阿芹,咱们走!”
这时,在屋子里嚎啕大哭的母亲手拿一根木棍,跌跌撞撞冲到张来福的身边,举棍要打张来福。正当棍子要落下的时候,秀芹用弱小的身体给挡住了。木棍重重地落在秀芹的身上。
秀芹“啊”的一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母亲手持木棍傻傻地呆站着,父亲也没了言语,也象根傻柱子戳在那里。
“爸爸妈妈,你们不想要我们活了,还不快过来救救秀芹,你们简直疯了。”张来福冲着父母大嚷。
吓楞的父亲听张来福这么一喊,没有了先前的嚣张,急忙上前给秀芹掐人中。好大一会儿,秀芹慢慢睁开了眼睛,脸色刷白,嘴角铁青,豆粒般的泪水汩汩儿下。这回该走人了,她也得以彻底解脱。
张来福伏在秀芹的身上呜咽起来。站在一旁的父母不知所措,没有了章程。
待秀芹稳定多了,张来福把她从地上抱起来,回他们的房屋里了。
张来福一边流泪安慰秀芹:
“阿芹,让你委屈了,父母真是……”他的泪水落到了秀芹的面颊上。秀芹仍在流泪。
不一会儿,秀芹感到头一阵比一阵痛的厉害,直恶心想吐,但又吐不出东西来。张来福想用自行车驮她到医院检查,可秀芹说浑身无力。张来福只身骑车去医院请大夫,走时也没有给父母打招呼。
张来福走后,公婆也没有了主意。婆婆悄悄来到秀芹的炕边,望着仍在流泪的秀芹,内疚地吐出三个字“对——不——起”。
秀芹没有答话,呜咽声大了起来。这时,公公也走了进来,没有说话,老两口面面相觑,叹气不止。
二十分钟后,张来福带来了医生。经过诊断,秀芹只是轻微脑震荡,无碍大事,用点药,多休息几天就会好起来。
那时,正值水泥厂销售旺季,单位脱离不开,张来福来到单位安顿好工作后,亲自去秀芹单位请假,又把大舅嫂接到家照顾秀芹,说了一大堆道歉的话。大舅嫂十分理解他的心情,安慰他说:
“别想那么多的事,这事我们都理解,你安心工作吧,有俺照顾,你放心。”
张来福又匆匆赶回单位,午间有应酬,晚上很晚才回来。
是夜,秀芹辗转难眠,进了张家这几年,经历了大喜大悲,人瘦了,心碎了,罪受了,尤其是近年来,看够了公婆的脸色,听腻了公婆的奚落,每天几乎都在流泪,心在流泪流血。她何尝不想早日做母亲,摆脱这尴尬的境地,然而不争气的身子让她备受箭熬,谁能替代她,谁能真正理解她的心。
劳累一天的张来福,简单问了秀芹的病情,不久就进入了梦香。望着熟睡的夫君,秀芹的心一阵酸痛。三十岁的汉子,为了工作、为了家、为了她,看上去显得老了许多。夫君承受的压力并不比她少,也许真的该给他生个孩子,可这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奢望,夫君命好苦,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了,否则影响他的事业,影响了家庭的团结,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她真的该走了,主动些,别再发生不愉快的事。
深夜,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,屋子里增添了许多亮光。秀芹下决心离开夫君,离开这个让她心碎的的地方。几次想推醒夫君,可夫君却睡得十分香甜。他太累了,心也累了,别惊动他,待天明再说吧。秀芹流着泪迷迷糊糊睡了。
天刚放亮,秀芹睁开发涩的眼睛,不见夫君,她以为夫君出去解手,可半个小时仍不见夫君归来。她强坐了起来,见炕头小凳子上放着一张字条,她顺手拿了过来。
“芹,这几天单位销售特别忙,许多合同需要我签字,好好在家休养,听话,按时用药,有嫂子照顾你,我很放心 ——爱你的的来福”
读着读着,她的手在颤抖,泪水浸透了字条,头痛了起来,她又躺下来,手中攥着来福的字条,可怎么也睡不着。
一个星期后,秀芹觉得身体好多了。她该上班了。他没有把情绪带到单位。
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是,起床后的秀芹含泪对张来福说:
“来福,谢谢你这些年了对我的关照和体贴,这家我不能再呆下去了,你放了我好吗?”
“芹,别说这样的话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来福替她拭去眼角的泪水。
“可,可我不能给你生孩子,你有事业,你的父母需要你,我不能太自私了,那样会毁了你,毁了你的家。”
“芹,可我舍不得你,要是那样,别人会怎么看我,骂我没有良知。”
“那你在父母那边也抬不起头啊,为了老人他们,你让我离开你吧。”
来福没有再说什么,泪水簌簌而下,紧紧地把秀芹楼进怀里。
少许,来福说:
“芹,这样吧,你先去兄嫂家小住一段日子,待我心情好了,咱们再商议好了。”
秀芹把头从来福的怀里抬起,“恩”了一声。
秀芹给全家做好了早餐,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,也就是随身换洗的几件衣服。饭后,她和来福一起来到兄嫂家。
兄嫂知道他们的来意后,谁也没有说什么。
当天的晚上,秀芹和兄嫂聊了许多许多……
一个星期后,张来福来兄嫂家欲接秀芹回去。秀芹硬是不肯。
“来福,这些天,我想了许多许多,咱们该分手了,也许你真的不愿意,可又没有别的办法,我不想让你有什么遗憾,那样我会更对不住你张家。”
“不能呀,秀芹,父母那边的工作我可以继续做,你别先提出来,兄嫂也不会同意的,那我怎么在兄嫂面前做人。”张来福显得有些急。
秀芹的大哥秀海说:
“来福呀,你是好人,没啥可挑剔的,但事到如今,如果大家都僵持下去,谁都不开心,妹妹都跟我说了。你也别再难为你父母了,父母也是为了你好,我们都是有知识有理智的人,将来还可以做好朋友处的。”
秀芹的大嫂接着说:
“他老姑父啊,这些年来,他老姑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,幸好有你呵护,你们夫妻感情很好,可是你的压力很大呀,你有发展前途,可不能让你家庭毁了你,和他老姑分手,也是一种没办法的解脱,我们不会怪你的。”
兄嫂如此通情达理,弄得来福不知说什么好,早先准备许多歉意的话都飞到九霄云外了。
兄嫂挽留来福在家吃了晚饭。
饭后,来福约秀芹到街街上匆匆,昏暗的灯光从居民家的窗户内反射出来,给黑漆的小镇增添了亮光。他们手挽手走在沙石街道上,脚步慢慢,都无心欣赏小城的夜景,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内心的苦涩与酸楚,高悬在天空的繁星不时眨吧眼睛,向人们诉说着不公平、不公正,就连那月亮也瞪圆了眼睛,吴公手持斧头不像在砍树,好像要把斧头砸向人间,砸碎那些束缚爱情、家庭的枷锁和迂腐的思想。他们在当时只有两道街、两条路的小镇上度来度去,很少说话。也就是在五年前的这段时间,他们相识相爱,可如今先前的激情荡漾无存,四目相对默默无语。
时候不早了,秀芹该回到兄嫂家了。至始至终,整个晚上,他俩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。可心里,秀芹找不到那种感觉。秀芹的心只有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知晓,可他们又能有何作为呢。常娥奔月那只不过是人间流传下来的一个美好的传说。她和来福的爱情故事又能流传多久,也许时间不会太长就会被人们淡忘。
来福把秀芹送到兄嫂家的院门时,欲言又止,紧紧地把秀芹搂进怀里,在秀芹的额头上、脸上亲吻起来,秀芹十分顺从,也许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吻。让他吻吧,吻个够吧,那样她才会少些内疚,少些痛苦,少些企盼……
两个月后的一天,秀芹和来福终于名正言顺地分手了。
当天下午,秀芹在来福的陪伴下回到了张家,很有礼貌地和公婆告别。
“请允许我再叫你们最后一次爸爸妈妈,秀芹我自进你们家这么多年,没有尽到义务,给你们二老增添了不少麻烦,我内存感激,以后会有更好的媳妇照顾你们,望二老多保重。”说完,秀芹眼含泪水头也不回,径直走出张家大院。
“阿芹,你……”
公婆再也没有说什么。的确也没有什么话要说的,然而,在张来福父母的心里,秀芹除了不能给张家传宗接代外,再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。望着走出院门永远不能再归来的秀芹,二老不禁伤感泪流。
“秀芹,你等一下,我送送你。”来福顾不上哭泣的父母,推上自行车撵秀芹去了。
秀芹没有坐来福的自行车,只是与他并肩朝兄嫂家的方向走去。整个路上,除了见熟人打招呼外,他俩谁也没有说话。
兄嫂见他们进来,知道了结局。兄嫂还是那样热情相让来福进屋坐。
进了屋,秀芹一头扎进炕里,用被蒙着头大哭起来,兄嫂、来福也泪水涟涟,在屋内玩耍的侄男侄女楞楞地站着,他们不知道大人之间发生的事。
哭吧,秀芹也该好好哭上一场,哭出来也许心情会好一些。
来福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兄嫂面前,痛哭流涕:
“兄嫂,都是我的错,我没有照顾好秀芹,让她在我家这些年受尽了委屈,恳求得到你们的谅解,希望你们好好照顾秀芹……“
秀海夫妇俩急忙劝来福起来,别吓着孩子。这时屋子里的侄男侄女开始哭泣。
来福跪在地上不起来,哭得象个泪人,一个劲儿道歉:
“秀芹,都是我对不起你,对不起,秀芹,啊……“
就这样,秀芹结束了这桩婚事。

责任编辑:媒体与法